在教育焦虑弥漫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看待教育的本质?教育应该追逐什么?又该如何实现我们的追逐?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执行校长徐加胜在其新书《教育的可能》中,给出了他的思考与回应。徐加胜用他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唤醒我们对教育更深层的理解——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彼此照亮。唯有找到教育真正的着力点,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才能与孩子彼此成全。
“教育就是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
记者:您的新书名为《教育的可能》。在您看来,当前教育环境中最被忽视或最需要被唤醒的“可能”是什么?
徐加胜:我在教育现场看到了很多大家遇到的困境,我特别渴望能够为这些遭遇困境的人提供一点点自己的帮助。其实陷入困境的也不仅是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从山东考到北京,来到北京四中工作,我发现自己作为教师所参与的教育环境和作为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有着非常大的冲突,这样一种冲突让我自己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诸多的困境促使我去思考,我想为这些遭遇困境的人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的教育经历也比较多元,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国内教育还是国际升学都有参与,所以我想把自己的思考与理解传递给大家。我相信只要保持独立思考,就一定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诸多问题,自然也包括教育问题。
记者:您能为我们分享一个在落实您教育理念的教育实践中,最成功或最具挑战性的具体案例吗?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徐加胜:这个最具挑战性的案例发生在我在北京四中璞瑅学校(以下简称璞瑅学校)任职的时候。2013年北京丰台区成立璞瑅学校,当时招收的学生大都是随迁子女,生源与北京四中是完全不同的,我很开心找到了一个契机去实践我的教育理念。
当时我33岁,我们招聘的老师也都是一群20多岁从北师大毕业的新人,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当时只有一个老同志,是从北京一六一中学退休的副校长夏洁,就是她带着我们一群年轻人去干。经过 3年的时间,璞瑅学校的学生不仅在成绩上达到丰台区排名第四的水平,在各方面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我觉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师生关系。我们会把情感层面的东西当成生产力,师生关系的质量有保障,才有教学质量。
我们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只有不到50人,毕业典礼时每一个学生都会上台唱歌并给学校送一个礼物,后来我们要把这些礼物都放进了校史馆,它们不贵重,但都有特殊的意义。还记得第一个上来的学生叫宗一江,他给学校留的礼物是一副眼镜。他说:“纵有万般不舍,我也即将离开我所深爱的校园。我把我初中带了 3年的眼镜留在这里,让它当我的眼睛继续去看这个校园的日升日落。”说完他就开始哭,我和台下的学生也开始哭。第二个学生叫陈炅,他带了一块精工机械手表,把手表指针调到了八点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校那时有一个塔楼,原本的设计是四面有钟,但因为没有钱,我们就做了个假的钟表,还把钟表得指针定在了8点半,象征孩子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是他们的。孩子们还给那个钟表起了个名字——“青春时钟”。陈炅把自己的手表定格在八点半来纪念那样一段时光,不论外部如何喧嚣,校园之内永远青春,永远八点半……这些难忘时刻至今回忆起来也仍旧感慨万千。
如果现在让我讲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几年,我一定会说是2013年到2018年在璞瑅学校那 6年。那 6年给我情感冲击力最强,我的成长也最快。教育就是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下,璞瑅学校的学生才一直保持着热情。即使在初三中考之前,你依然能看到孩子们和老师们一起在操场上奔跑,他们和老师们的关系很融洽,也愿意和老师一起努力朝着目标前进。这就是我所说的高质量关系,它能带给孩子生命层面的成长,而成绩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外显成果。
“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记者:您倡导教育要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要秉持长期主义的教育观,这对教师的角色和教学方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学校管理者又如何为教师创造支持这种转变的环境?
徐加胜:我所看到的现状是大多数的孩子都缺乏独立人格。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父母和师长过多的安排和替代。我们知道了原因,那么解决的方案也非常简单——最重要的就是“放权”,我们要把一些原本由孩子来安排的事情交还给孩子自己。
我们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去替代孩子做决定?是因为我们过于追逐眼前结果的完美。所以,要想放权,就要放弃眼前干预下的完美,那是一种假象。为了让孩子具备真正独立的能力,我们就需要陪伴孩子进行大量的阅读、开阔的行走、充分的交流。在此基础上,适当地放权,给孩子试错的机会,他们会慢慢地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独立人格不是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而是慢慢地生长、慢慢地呈现的。
记者:在教育的过程中,您也十分重视高质量关系的建立。对于家长而言,建构这种高质量关系需要做出哪些转变?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
徐加胜:对于家长而言,建构高质量关系首先需要理解它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孩子和师长的关系,还有和同伴的关系。亲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根本的,父母对孩子有非常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能力和品德方面,更是在情感依托方面。
我们常有一个误区,认为孩子自信或者不自信是能力问题导致的。很多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不好,就会不自信、不快乐,在意成绩会对孩子本身有影响,所以才在乎孩子的成绩。然而,一个人在能力的比拼中获得自信,这肯定是个骗局,因为你总会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能力是没有尽头的。其实,一个人自信的关键取决于在亲密关系中被认可的程度。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让孩子一生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单纯被外部衡量的对象,他总需要在某些关系中获得无条件的支持,所以这可能才是亲子关系的重要所在。
师长和同伴,是在孩子身边陪伴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人。这些人都在潜移默化地去影响着这个孩子,所以,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成长最关键的其实不是分数,而是他身边有一群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说第一个要说的人和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质量更高,孩子的成长就更顺畅。
第二个维度是人与文明的关系。孩子们跟随书籍在几千年的文明里去徜徉,去接触那些有趣的灵魂,和他们产生互动,进而慢慢地了解生命的意义。
第三个维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孩子要和大自然充分的亲近,对于其生命感受、精神的丰富和他对外部挫折的抵抗能力,都会有极大的作用。
所以对于家长而言,要想建构高质量的关系,就应该想办法把孩子带到山水中、带到自然中,通过阅读带到历史文明当中。要重视孩子和父母、老人、师长同伴的关系,而不能把孩子局限在一个只有分数和练习的世界里面。
记者:在国际教育领域,家长也面临很大的升学压力和焦虑。作为校长,您如何与家长沟通,引导他们更关注孩子的长远发展和内在成长,而非仅仅聚焦于短期升学结果?您认为学校在缓解家长焦虑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徐加胜:能不能有一个最终解或正确解我不知道,但我们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第一就是沟通。老师要多和家长去沟通,可能问题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沟通了,就是沟通不好呢?我觉得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取决于家长和老师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比沟通更重要的是双方先确定价值观,明确我们教育孩子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吵成一锅粥,还吵不出一个共识。
家长为什么会焦虑、容易陷入“内卷”?是不是怕孩子跟不上别人?我想要告诉家长的是,孩子跟不上别人是正常的,尤其在某一个特定的赛道、特定的领域,跟不上就是常态。
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就陷入“比较”的怪圈里。我们要知道,人世间一些独特的感情,比如亲情、爱情,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不必要的比较和衡量。当家长能够理解并容许自己的孩子在很多地方不如别人的时候,也许就不会陷入这样的“死循环”了。
这时候可能有家长就会问,那我什么都不要求孩子算不负责任吗?家长可以发力,在那些最基本的规则和习惯养成上发力,在求而得之、舍则失之的层面发力,你可以要求孩子做一个不说脏话的孩子,做一个见了长辈要打招呼的孩子,做一个满怀善意的孩子,这些都不困难。但如果家长非要在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地方较劲,那肯定是痛苦的。家长总是给孩子设立一个可能无法达到的高度,或者在某个技能层面必须达到的程度,最终消磨的只能是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可能有许多家长都听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让你生我了吗?你也没跟我商量”。我们老觉得这句话很荒谬,但作为家长,我们也得明白这么荒谬的一句话背后,它得有多少痛苦的忍耐和无情的消磨。
教育是指向未来的,指向孩子未来长远的幸福的,眼前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未来全面均衡的发展、身心的愉悦而铺垫和积累的。所以我始终相信,一个拥有良好素养、拥有独立人格、和父母有良好互动、有良好习惯的孩子,他的成绩一定不会差,他的未来也一定不会差。教育从来不是让一个孩子超越自己的天赋,成长为一个家长心目中“那个优秀的人”,而是成为“他自己”,成就他生命的一种可能性。
“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记者:您如何理解“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之间的张力?
徐加胜:我觉得目前最应该保留的是基础育领域的秩序感和大家身上普遍都具有的努力和勤奋。我们借助勤奋和秩序感可以达成一个非常高效的基础教育的效果。最应该打破的,是对于升学结果的执着。这是一种极为短视的状态,站在孩子未来长远发展的角度,这会让我们失去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
记者:您对未来中国教育走向的“更多可能”抱有什么样的期待?您最想对正在教育道路上探索的同仁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徐加胜:为人师长者要反复而深刻地叩问自己的灵魂,我们到底怎样做才是为孩子好。我们的心知道答案,问题是要真正找到我们的心。
如果在教育中,我们能够引领学生将求知树立为自己的信仰,能够有持续的学习行为,在求知的过程中充满着激情与愉悦,不会为功利所惑而突破底线。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一定会非常成功。
求知成为学生的信仰,教育成为师长的信仰,在信仰里,我们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完成真正的自我实现。成为一个有自我认可,有崇高感的生命,这是一份难得的幸福。
宋代儒生张载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史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第一篇文章的名字——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教育就是这样的事业。
(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彭诗韵 采访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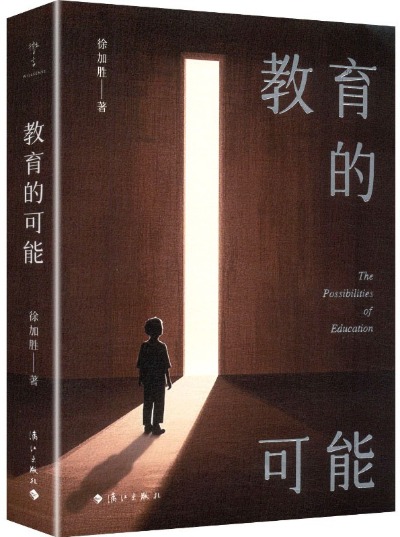
《教育的可能》
徐加胜 著
漓江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工信部备案号:京ICP备05071141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24
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 中国教育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下载使用
Copyright@2000-2022 www.jyb.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