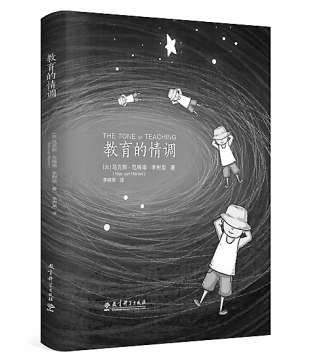
《教育的情调》 [加]马克斯·范梅南 李树英 著 李树英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在浩如烟海的教育论著中,有一些作品因其体系宏大、逻辑严谨而成为学科的基石,另一些则以其思想温润、文字隽永而成为教育者灵魂深处的知己。《教育的情调》无疑属于后者,自2019年出版以来,这本小书就一直深受教育研究者,尤其是广大一线教师和家长的喜爱,成为教育经典的畅销书。它不以系统建构或概念定义来进行学理思辨,而是以一种教育现象学方式,如诗如散文般地探究“机智”“关爱”“希望”等教育实践中最微妙也最核心的元素。
初读此书,我们或许会惊叹于其文字的优美与洞见的深刻,感到如沐春风。然而,对此书真正的尊重与最有价值的阅读方式,绝非仅仅将其“读薄”,即提炼出几个核心观点或精彩语录,而是将其“读厚”——用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教育实践、困惑反思去与之对话、碰撞、交融,最终在作者勾勒出的轮廓里,注入属于自己的血肉与色彩,读出独一无二的“我”的教育情调。
所谓“将书读厚”,本质上是一个从“输入”到“建构”的能动过程。它要求读者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积极的思想参与者和意义创造者。对于《教育的情调》这样一部充满留白与张力的教育著作而言,这种阅读方式尤为契合。作者并未试图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操作手册。作者所做的,是试图唤醒我们内在的教育感知力。
因此,将这本书“读厚”的过程,可视为一个三层递进的建构之旅:第一层是“印证与唤醒”——用个人实践去充实书中的情境;第二层是“诘问与深化”——用现实困境去拓展书中的论述;第三层是“融合与创造”——在理论与实践的交响中,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行动自觉。
为“情调”找到注脚
《教育的情调》论述的核心概念,如“机智”,是无法通过定义来精确捕捉的。书中将其描述为“一种即时的、敏感的、临场的、机智果敢的行动能力”,这样的描述固然精妙,若无亲身体验的印证,难免显得悬浮,终究只是一个优美而模糊的词。
将书“读厚”的第一步,就是要主动开启记忆的闸门,用那些鲜活的、曾被我们忽略的教育瞬间,去为这些“情调”寻找生动的注脚。
当我读到“机智”时,脑海中浮现的不再是抽象的定义,而是具体的画面。我想起一位年轻教师的公开课: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孩,在回答问题时突然卡壳,满脸通红,台下听课的老师们开始窃窃私语,气氛十分尴尬。这时,那位老师没有催促,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微笑着对那个男孩说:“别着急,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有点儿害羞的朋友,需要我们多一点儿耐心去等待它开口。你刚才的思考已经离它很近了,要不你先坐下,我们让思想再飞一会儿,待会儿它可能自己就跑出来了。”全班同学都会心地笑了,紧张的气氛瞬间化解。那个男孩如释重负地坐下,眼神里充满了感激。这一刻,这位老师的行为完美地诠释了“机智”:它包含了对学生自尊的呵护(关爱),对教育节奏的把握(分寸),以及对学习过程的隐喻式理解(智慧)。
同样,在读到“希望”这一情调时,我不再仅仅理解为对学生未来的期盼,而是想起了自己曾面对的一个学生。他纪律散漫,成绩垫底,几乎所有老师都已放弃。但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我发现他对航模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专注,于是就鼓励他参加科技比赛,帮他寻找资料,甚至允许他在完成基本作业后,在教室一角制作模型。起初,这并未对他的学业成绩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能看到,每当他谈论起空气动力学时,眼中闪烁的光芒。那光芒就是教育的“希望”所在——它并非源于对一个标准化的“好学生”的执着塑造,而是源于对一个独特生命潜能的发现与守护。我坚信,这份由热爱点燃的专注与自信,终将迁移到他生命的其他领域。
通过联想这些真实的教育体验故事,书中的“关爱”“责任”“分寸感”等概念,便不再是纸面上的文字,它们被我们过往的成功、失败、喜悦、遗憾逐一激活,变成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的存在。这个过程既是对作者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是对自我教育实践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肯定。
与作者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真正的阅读,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批判性的对话。将《教育的情调》“读厚”,意味着要敢于用我们身处的现实困境去“诘问”作者,从而深化我们对教育复杂性的理解。
例如,作者强调教育者需要有“耐心”和“分寸感”,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与时间。然而,当一个班级里有五十多个学生,而教学进度表和标准化考试的压力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时,一位老师如何才能从容地等待一朵花的缓慢绽放?当“双减”政策意在减轻学生负担,而家长与社会的“剧场效应”却愈演愈烈,将焦虑层层传递时,我们又该如何安放那份教育的“希望”与“平常心”?
带着这些困惑去重读《教育的情调》,我们会发现,它并非一本不食人间烟火的乌托邦式吟唱。它恰恰是在提醒我们,“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张力中进行创造性的平衡”。于是,我们可以与作者展开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
“先生,您所说的‘机智’,在面对一个因家庭变故而行为叛逆的学生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包容他的一切,哪怕这会扰乱整个班级的秩序?这里的‘分寸’边界何在?”
“您强调的‘关爱’,在面对一个需要被严格要求才能激发潜能的学生时,是否与‘严格’必然对立?充满关爱的严格,其‘情调’又该如何体现?”
这些诘问,并非为了否定作者,而是为了将他们的思想置于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境中进行检验与延展。这样的思考,迫使我们不能满足于书中那些田园诗般的案例,而去探索“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葆有教育的情调”。我们会开始思考,如何在紧张的教学进度中,通过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次课间十分钟的真诚交流,来传递关爱与机智?如何在必须进行的严肃批评中,注入对学生人格的尊重与未来的希望?
通过这种诘问式的阅读,我们将书“读厚”了,因为我们把个人无法化解的现实矛盾、把整个时代教育的焦虑与困惑都带入了书中。这本书从一本关于个体教育智慧的小书,变成了一个承载我们与时代进行教育博弈的广阔平台。我们不再仅仅是《教育的情调》的读者,更成了与作者并肩思考的同行者,共同直面教育那“令人愉悦的复杂性”。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交响
阅读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是将所思所感内化为行动的自觉,外化为独特的气质。在经历了“印证与唤醒”“诘问与深化”之后,我们将《教育的情调》“读厚”的终极目标,便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交响中,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最终创造并弹奏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情调。这意味着,书中的“情调”将不再是我们刻意模仿的某种行为范式,而是自然流淌在我们教育教学血液里的品格。
一个活出自己教育情调的教师,他的“关爱”不再是写在教案里的目标,而是在看到学生微蹙的眉头时,会下意识地放慢语速;他的“机智”不再是某种临场技巧,而是在面对课堂突发状况时,能幽默而从容地化解,并将其转化为一个新的教育契机;他的“希望”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学生,都能由衷地相信其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并用行动去浇灌。
我认识的一位物理教师,他的教育情调便充满了“科学的浪漫”。他会在讲到万有引力时,对学生们说:“牛顿发现的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种宇宙级的浪漫——是同样的力,让苹果落向大地,也让星辰拥抱彼此。”他会在实验室里,引导学生感受电流穿过导线时细微的嗡鸣,称之为“能量的歌唱”。他从未刻意去说“我要运用教育机智”或“我要表达教育关爱”,但他的言谈举止,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教育情调。他无疑已经把《教育的情调》这本书“读”进了课堂,他将科学的理性之美与教育的人文之光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风格。这便是将书“读厚”后,最动人的果实。
《教育的情调》如同一张意蕴丰富的乐谱,作者为我们谱写了主旋律,而真正的演奏者是我们自己。将这本书“读厚”,就是拒绝成为一个被动的识谱者,而是要勇敢地拿起我们各自的“乐器”——我们的知识、体验、情感与人格,去与这旋律共鸣、对话,乃至进行即兴创作。我们用自己的故事去印证它,让抽象的理论拥有了具象的血肉;我们用时代的困惑去诘问它,让理想的图景接上了现实的地气;最终,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将这份理解与思考,沉淀为一种稳定而独特的教育人格,一种属于“我”的教育情调。到那时,我们手里的这本书或许早已泛黄,但我们心中的那本“教育之书”,却愈加丰厚、坚实,并且散发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15日 第09版


工信部备案号:京ICP备05071141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24
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 中国教育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下载使用
Copyright@2000-2022 www.jyb.cn All Rights Reserved.